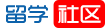在爱尔兰留学,除了平时的学习、休息,也能发生不少新鲜事。那次,偶然遇见一位爱尔兰的伯爵是我难忘的一件事。
在爱尔兰的几天里,始终觉得这里是通往天堂的最后一站,一望无际的绿色缓坡,天空始终阴霾,乌云夹带着一丝白云静静地翻滚。脑海里一直回响着恩雅的音乐,颂经般悠远空灵,这样的地方必然产生这样的音乐。
这天坐了一上午车才到了古堡,所有人都以为这不过是欧洲众多古堡中的一个,情绪索然。好在古堡快餐店的烤三明治味道不凡,慰藉着我们劳顿的神经。
正当我们大嚼烤三明治的时候,他出现了。粗花呢外套,看上去年纪不小了,领子已经长了皱纹,帆布裤嫌短了些,裤腿上一个巴掌大的三角口,用粗粗的黑线撩了几针。浑身上下没有一件新行头,却挡不住逼人的气魄。身材匀称,腰板笔直,头发花白,五官结构属于那种很好看的外国老头,不管是架副眼睛、挂根手杖、戴个鸭舌帽,或者有意无意系条围巾,绅士那套行头都跟他很登对。但是他没有这些零件,只是将白皙修长的手指交叉着放在胸前,眼风到处,热情而得体。“这位老先生,气质真好!”大家啧啧称赞,直至此时,我还以为他是退休的科学家,因为我们要参观的是爱尔兰历史科学中心。
当知道这位原来是真正的伯爵——第13代帕逊伯爵的时候,便越看越顺眼。有人明明是草民却把自己当贵族对待,而真正的贵族在扮演平民——当然,谁也学不像对方。
帕逊家族的贵族各个都是杰出的科学家: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是由第三代伯爵在1840年设计建造的;第三代伯爵的儿子发明了蒸汽涡轮发动机,伯爵夫人则是位女摄影师;到了第四代伯爵,他开始测量月球表面的温度;第6代伯爵及伯爵妇人致力于园艺建设,使这个30多公顷(1公顷=660亩)的庄园一跃成为欧洲最美丽的庄园之一。
如今,眼前的伯爵已是第13代,他以祖上的功绩为主要内容,成立了这个爱尔兰历史科学中心。建于1850年的老楼里,展示的是这个家族的发明和用具,从显微镜到生锈的锅碗瓢盆,可惜我们都是俗人,看来看去得出的结论是:房子大就是好,什么都能留着!
以前在电影中看到过庄园,只知其大不知这“大”的概念。走出爱尔兰历史科学中心,已经有两辆漂亮的马车和同样漂亮的车夫在等候了。坐在马车上,伯爵左手一挥:“这是爱尔兰最古老的吊桥,建于1820年!”右手一挥:“这是第二代伯爵挖运河时候顺手造的湖,那是19世纪的冰库,城堡一年使用的冰块和肉都存放在这里。”
左手再一挥,指着一棵开满白色花朵、粗壮的大树:“这是我父亲从四川带回的木棉树,是用火车从西伯利亚运过来的!”右手拉过一条树枝:“这是我从云南带回来的,一共去过两次云南,带回很多花和树!”
坐着马车匆匆一圈走下来,仿佛从自然保护区钻了出来。下车的地点,一边是天文台,巨大如炮筒般的望远镜依然架在那里;另一边,一大片草场之后,城堡仿佛耸立在云端。
从此开始,不能拍照。作为世袭的称号,目前欧洲还有不少爵爷,但是依然住在城堡里的却不多了,帕逊家族从1620年开始一直都住在这个建于1170年的城堡里。城堡不对外开放,但是今天伯爵很开心地带我们参观古堡,因为我们和他钟爱的植物一样,都来自中国。
像所有城堡一样,大门十分厚重高大,推开15度角,就有惊天动地的效果,每人侧身而入。
大厅里有种发霉的味道,脚下的真丝地毯已经破旧黯淡了,墙上挂着先人的肖像,壁炉上挂着鹿头和猎枪。所有陈设仿佛都打着时间烙印:400年!
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柜,摆满了陈旧的书,其中一本竟然是厚如辞海的《中国花卉大全》,是伯爵从中国背回来的。这时,一面书柜突然晃动起来,在大家惊愕之际,一位满面笑容的老妇人竟走了出来!哇,贵族家真的有许多暗门!而这位衣着如邻家老太的老妇人就是伯爵夫人!意外之下,差点条件反射地拎着衣襟行个蹲安!
休息厅的三角钢琴上,摆满了黑白和彩色的照片,都是历代伯爵的家人。房间里到处都是精美的摆设,看得人眼花缭乱,还有一架优美的竖琴。午后的阳光穿透高大的窗户——虽然不是落地窗,但是架不住层高足有5米!阳光笼罩在每一件工艺品上,可以看到上面的灰尘甚至是蜘蛛网。窗外远处是一条河,以及一望无际的绿色植被。想象着,400年前,伯爵和伯爵夫人坐在这里用下午茶,远处河水汩汩流淌,爱犬与爱子在草地上任性地玩耍,训练有素的仆人静立门边……所有一切都是他们的!
伯爵很节制地展示他的“豪宅”,大家则小心翼翼,生怕碰坏随处可见的工艺品。而我则紧紧抿住嘴,惟恐提出孟浪的要求:“伯爵大人,我想看看您的密室和地牢!”
城堡之旅很快就结束了,如果能在城堡里住一夜,如果能亲手去掉竖琴琴弦间的蛛丝,如果能掀起破旧的真丝地毯看看下面是否藏着字条,如果能在密门之间多走几个来回……
对了,伯爵的儿媳妇是天津人,与伯爵的儿子住在北京。这意味着,下一任伯爵夫人将是一个中国女子,她将拥有这一大片土地,住在这古老的城堡中,被人称为countess(伯爵夫人)——太神奇了!